一、凯风自南,翼彼新苗
善于发现新人,培育新人,奖掖新人,这是“文评”数十年来的优良传统。不以名声地位取人,而从文章本身取人,几代的文评编辑,都秉持着这种理念。尤其是在那些车载斗量的稿件是发现新人的有前途之作,“文评”的编辑慧眼擢拔,认真点拨,使很多新人脱颖而出,成为日后的著名学者。在这方面,我的体会尤为深切。1984年,我从吉林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到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虽然我的硕士专业是古代文学,方向是唐宋文学,但我的导师公木(张松如)、喻朝刚和王士博教授都是以理论见长的学者,读研的时候都深受濡染,培养了浑厚的理论兴趣。到辽宁师大虽然是在古代文学教研室,但是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角度,往往带着明显的理论色彩。1986年我写了一篇《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交融——温庭筠乐府诗简论》的文章,试着投给了《文学评论》编辑部。这篇文章篇幅很长,有一万五千多字。是以系统论和价值学的方法来分析温庭筠的乐府诗的。自己觉得有些新意,但对能在“文评”上发表没抱什么希望。我和“文评”的编辑老师们从来没有任何接触,也不知道都是姓甚名谁,只是看着刊物后面写的地址“北京市建内大街5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直接邮过去的。我当时连讲师都还不是,只是个硕士刚毕业不久的助教而已。过了几个月时间,我突然接到了“文评”编辑部陈祖美老师的亲笔信,大意是说文章有内容,有新意,发人所未发,准备刊用。但是要作相应的修改。且前面刚刚发表过杨海明先生论温词的一篇文章,因为是同一个作家,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我看了祖美先生的信非常激动,马上写了回信表示要按着编辑老师的意见认真修改。几天内就把文章的修改稿寄回给编辑部了。到1987年秋天,突然在系资料室看见刚到的《文学评论》第五期上我的文章发表出来了,高兴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后来我在编辑部给我寄来的样刊的扉页上,用毛笔隶书体工工整整地写下了杜甫的两句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在文章发表出来之前,我还不知道祖美先生是男老师还是女老师。直到应邀参加《文学评论》编辑部主办的会议(记得是在杭州)上,我才第一次见到这位风姿高秀的著名女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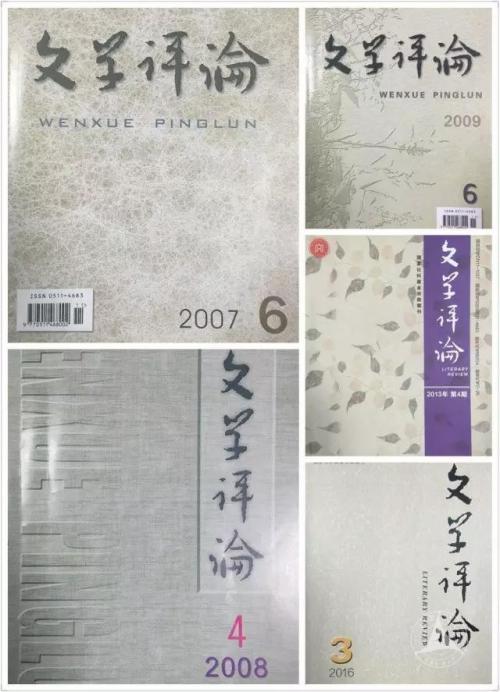
“文评”给我发表的这篇文章,对我的激励是非常大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我的学术研究方向的一种肯定。在那几年时间里,我用了很多功夫来阅读理论经典。包括西方的和中国的,包括哲学的、美学的。对于西方近现代美学著作也用力甚勤。从理论的角度来观照中国古代文学作家作品,得到了许多新的“景观”,也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学术特色。这种学术路数,也得到了后来任“文评”古典组长、乃至“文评”主编的胡明老师的认可。胡明老师博见多识,思想敏锐,目光犀利,他本人就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优秀学者。在“文评”鼓励下,我对学术研究有了越来越浓的兴趣,也对理论学习和研究越发投入,研究对象仍是中国古代诗学。在“文评”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后,我更勤于思考,努力写作,评讲师的时候已经发表了二十几篇论文,其中有《文学评论》和《文学遗产》这样的名刊的文章。之后我又写出了《情感体验的历程:中国古典诗歌的原型意象》的长文,又投给了“文评“编辑部。这篇文章是用西方的原型批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诗歌。虽是以西方的理论为方法,我特别注意不要生搬硬套地运用西方理论,而是借它山的石,攻自己的玉,将其改造为适合研究中国的文学传统。这篇文章得到胡明老师的欣赏和鼓励,他在来信中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指出文章中关于对文学典故的分析,之前葛兆光先生发表过的《论典故》一文中的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建议重新考虑那一节。我按着胡明老师的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文章发表在《文学评论》1990年2期上。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好的反响。由于我在那几年的学术研究上表现出来的势头和理论特色,被文艺学专业看好。系主任曲本陆教先生本身就是文艺学专业的教授,他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愿意由古代文学专业转到文艺学专业,以作为这个专业的接续力量。当时的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就是以后的文学院),以文艺学专业的学术实力最强,有几位享誉国内学术界的著名学者,如:冉欲达教授、叶纪彬教授、曲本陆教授等。在80年代末期就有了硕士点。我对这几位文艺理论家充满了敬意,于是欣然同意转到文艺学专业。89年的政治风波我受到了冲击,本来已准备破格提升副教授的事也停下来了。但我刚到文艺学教研室,就开始带研究生了,当时还是讲师的身份。这当然要感谢“文评”编辑部的老师们。我这个当时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读书与工作都不在北京,开始在文评发表文章时,与编辑老师都素昧平生,却得到了“文评”的发现与擢拔。在学术道路上能满怀热爱地走了30年,正是源于开始的时候,“文评”给予我的信心和鼓励。在《情感体验的历程:中国古典诗歌的原型意象》一文发表之后,我又在陶渊明诗中看到了魏晋玄学的痕迹。于是又花了很多时间研读玄学,并写出了《陶诗与魏晋玄学》的长文。我在当时住在学校分给我的筒子楼(亦称“五七楼”)里,一共不到40平米,分成了一大一小两个房间,小间大约有不到6平米,是我的书房兼卧室。厨房和厕所在一起,大概有四米的见方,住筒子楼的同事戏称,可以蹲在厕所里直接炒菜。我读陶诗读出了味道,灵感迸发,下笔不休,只有2天时间就写出了一万五千字的文章。写完后又寄给了“文评”。当时由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著名学者曹道衡先生任负责古典文学的副主编,他看了之后十分欣赏,只有3个月时间就把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了,发表在《文学评论》的1991年2期上。对我来说,当然又是极大的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