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由中国传媒大学英文期刊Global Media and China编辑部与中国传媒大学移动互联与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后疫情时代下的全球媒体与中国”国际高端网络论坛顺利举行。此次网络论坛分为主旨演讲和圆桌讨论两部分,围绕“后疫情时代下的全球媒体与中国”主题,聚焦于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与全球媒体在后疫情时代下的批判研究和学理探索,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讨论自疫情爆发以来媒体领域内涌现出的诸多现象以及后疫情时代下全球媒体的发展与布局。
论坛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段鹏教授主持。参会的各位国内外传媒学界嘉宾包括上海交通大学李本乾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姜飞教授、香港中文大学Anthony Fung教授、南加州大学Stanley Rosen教授、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Terry Flew教授、澳大利亚科廷大学Michael Keane教授、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Jeroen de Kloet教授、英国卡迪夫大学Stuart Allan教授、英国伦敦大学学院Tim Jordan教授、香港浸会大学John Erni教授、SAGE资深编辑James Skelding Tattle、科睿唯安高级市场经理赵冲先生、中国传媒大学张磊教授、韩霄副研究员。段鹏副校长代表中国传媒大学向前来参加本次网络论坛的同仁和师生表示热烈欢迎。

第一场主旨演讲主题为“全球媒体应对‘信息疫情’的经验检视”。香港浸会大学John Erni教授作了题为《制定文化权利:以少数民族媒体与文化参与为例》的分享,讨论了“媒体与文化参与”在发展社会资本和少数民族弹性的文化认同中的作用。研究基于定量调查、定性文化指标研究和批判性文化映射研究的方法,研究分析香港少数族裔在互联网上参与媒体、艺术和娱乐活动的情况。研究发现,少数族裔青年的社交能力、社交资本和文化认同往往使得文化权利的制定过程变得复杂。对以上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可以进一步探索阻碍少数族裔进行文化融合的因素。


美国南加州大学Stanley Rosen教授围绕《好莱坞在中国、中国在好莱坞:疫情过后双方能重归轨道或关系有变?》主题进行了精彩演讲。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加速造成了中国与好莱坞的分道扬镳之势。好莱坞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迅速下降,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大力进行本土电影创作。但诸多问题也导致中国创作的电影难以融入国际市场。疫情为中国本土电影创作者带来了机会,但如何展现中国特色、讲好中国故事,与好莱坞“大片”势均力敌、相互角逐还是任重而道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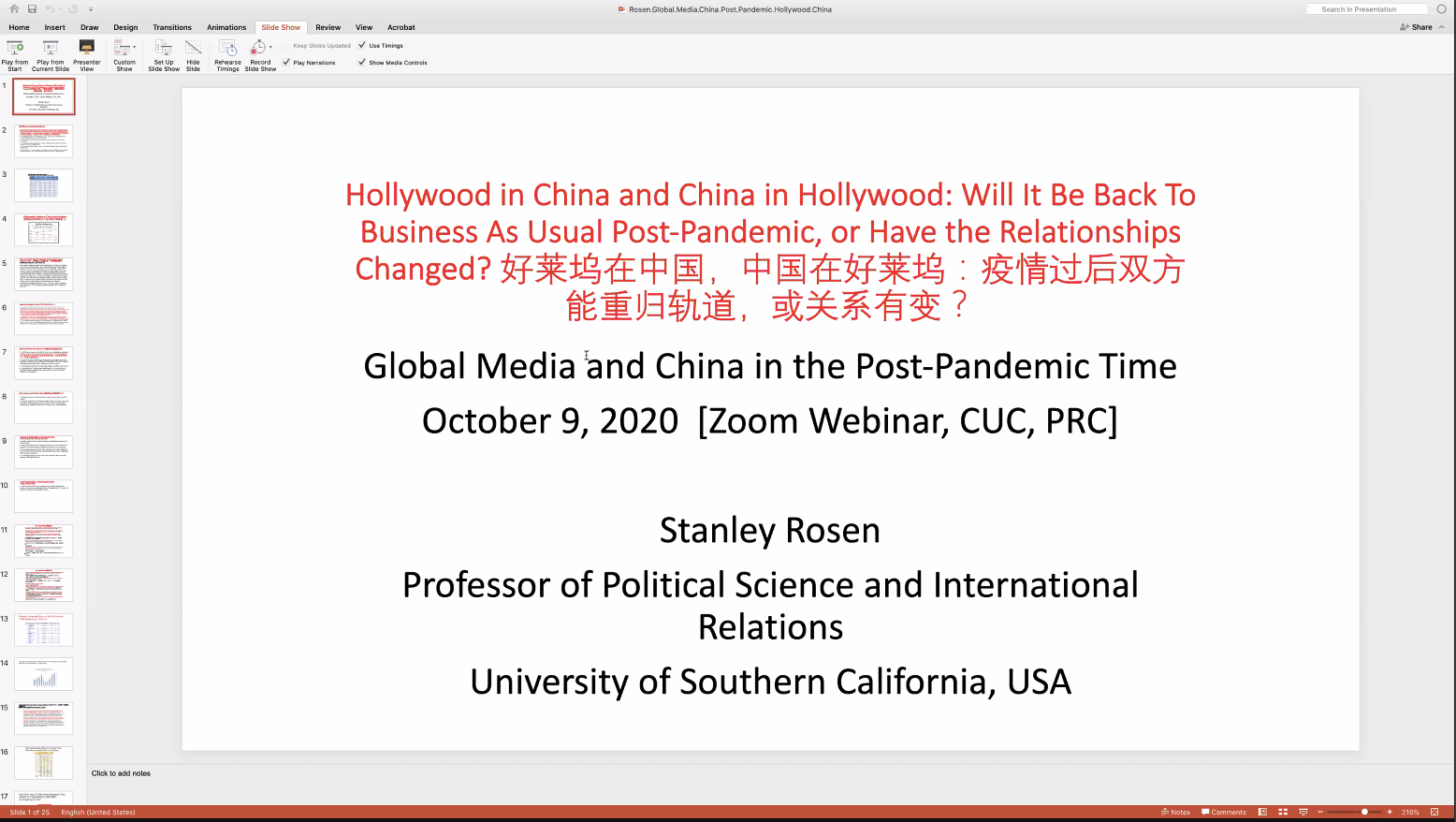
上海交通大学李本乾教授针对2020中国传媒国际竞争力研究展开了阐述。该研究通过中国传媒产品和服务与全球187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产业、全球75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上市公司的各项数据对比,来分析中国传媒产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李本乾教授还为提升中国传媒国际竞争力提供了七条策略:资源开发战略、价值链生态战略、内容创新战略、融媒体战略、传媒企业提升战略、传媒人才战略和传媒体制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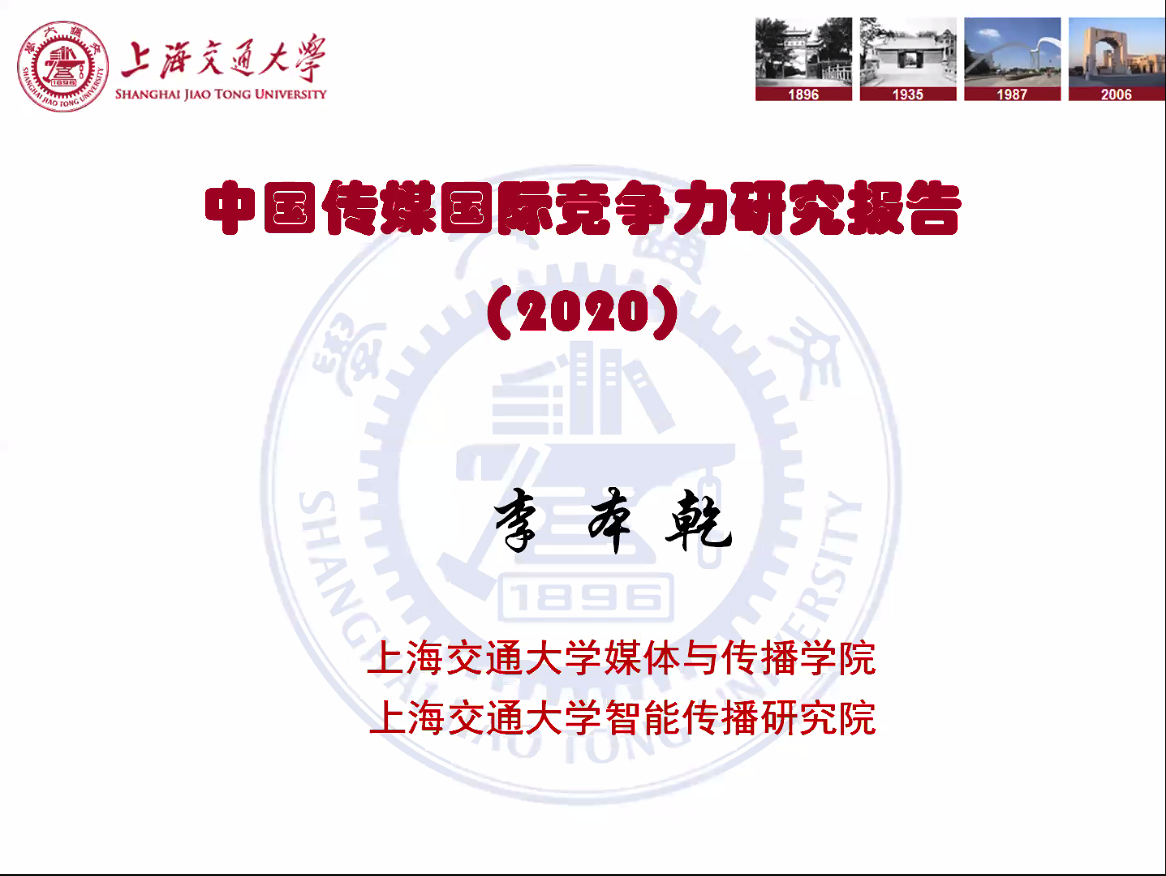
北京外国语大学姜飞教授以《后疫情之后:国际传播信用结构性变迁》为题进行了演讲。近五年来,西方部分国家试图削弱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国际传播的滥用、缺少交叉验证而导致的观点聚合生产机制的失衡让现有的信息传播成为一个由“政府——媒体——公众——政客——政府”组成的闭环,严重影响了可信的信息传播机制的重建。在后疫情时代下,中国需要综合“after”“post”“critique”三个层面来考虑“后”疫情时代的“后”字所带来的难题,并重新思考和设计自己在世界眼中的形象。

中国传媒大学张磊教授的演讲主题为《社会减速与媒介时间性》,结合罗萨的加速理论与疫情期间社会的隔离与封锁对“社会加速,社会减速”展开了探讨。时间的观念随着社会的进步产生了一些进化,由农业社会自然时间(农业社会)、时钟时间(工业社会)到现在的媒介时间(信息社会)。在媒介时间性概念上,“时间的权力”究竟归属何方?这需要基于政治经济分析后进行一个哲学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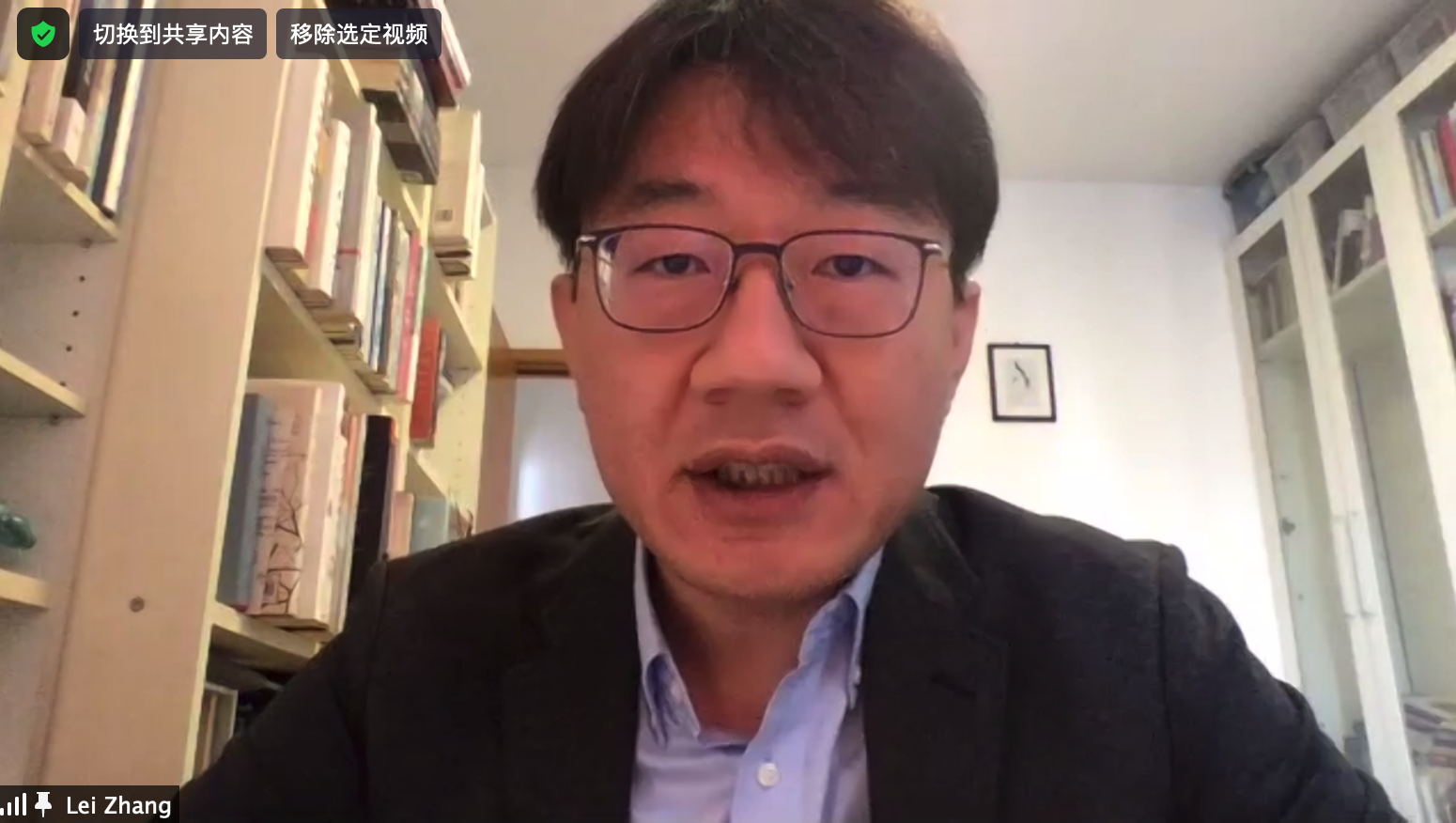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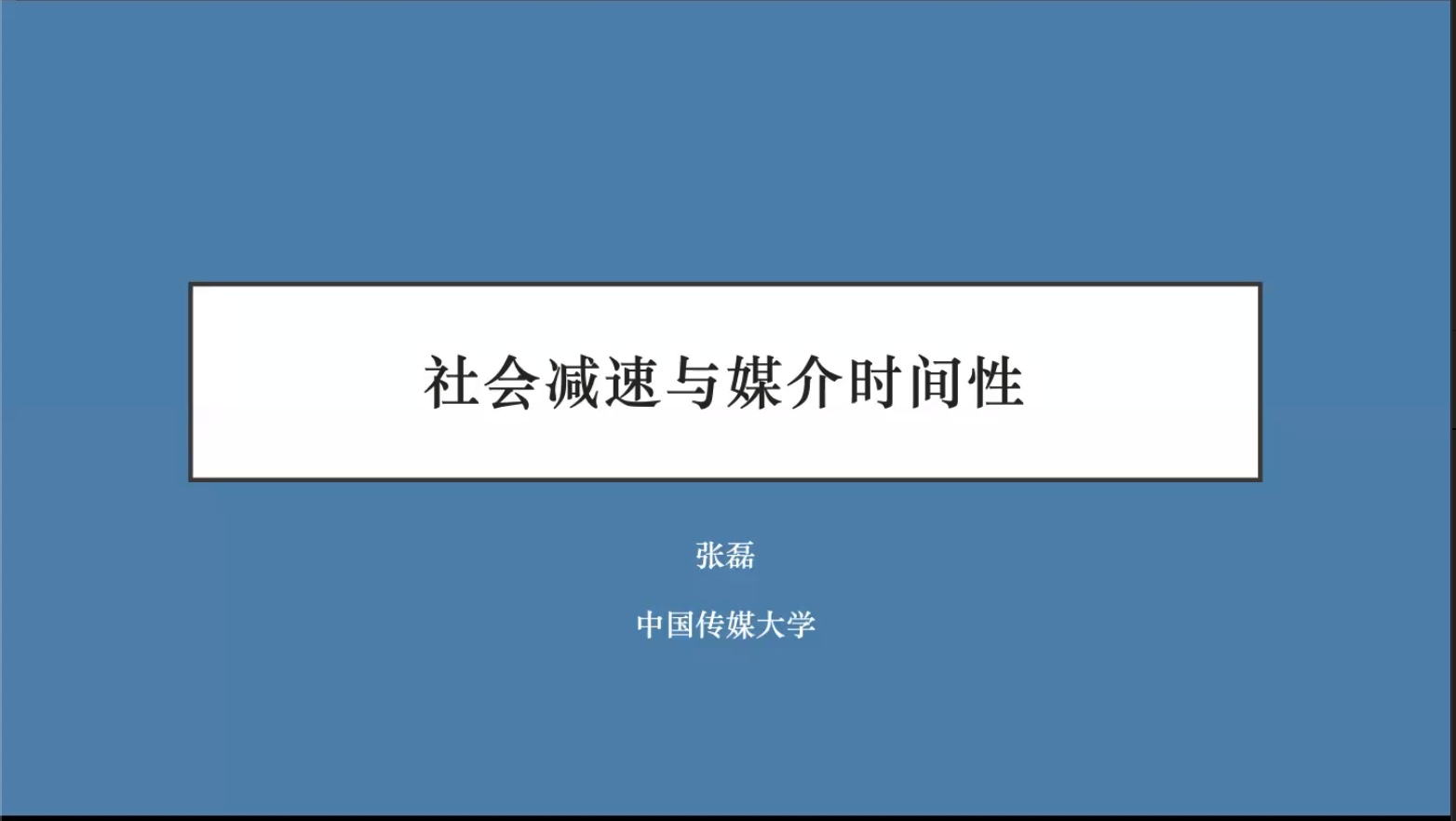
当日下午举办的第二场主旨演讲——“后疫情时代下媒体传播的新趋势与特点”由张磊教授主持。香港中文大学Anthony Fung教授就《创造性工作是虚构的吗?网络小说作家的劳动条件》进行了主题演讲。该研究通过收集近四百位网络小说作家的问卷,分析得出——网络小说作家这份顶着“创意”名号的工作,背后暗藏的却是资本的剥削。许多作者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和不稳定的劳务关系进行小说的写作,但他们却享受这种充满世界主义的生活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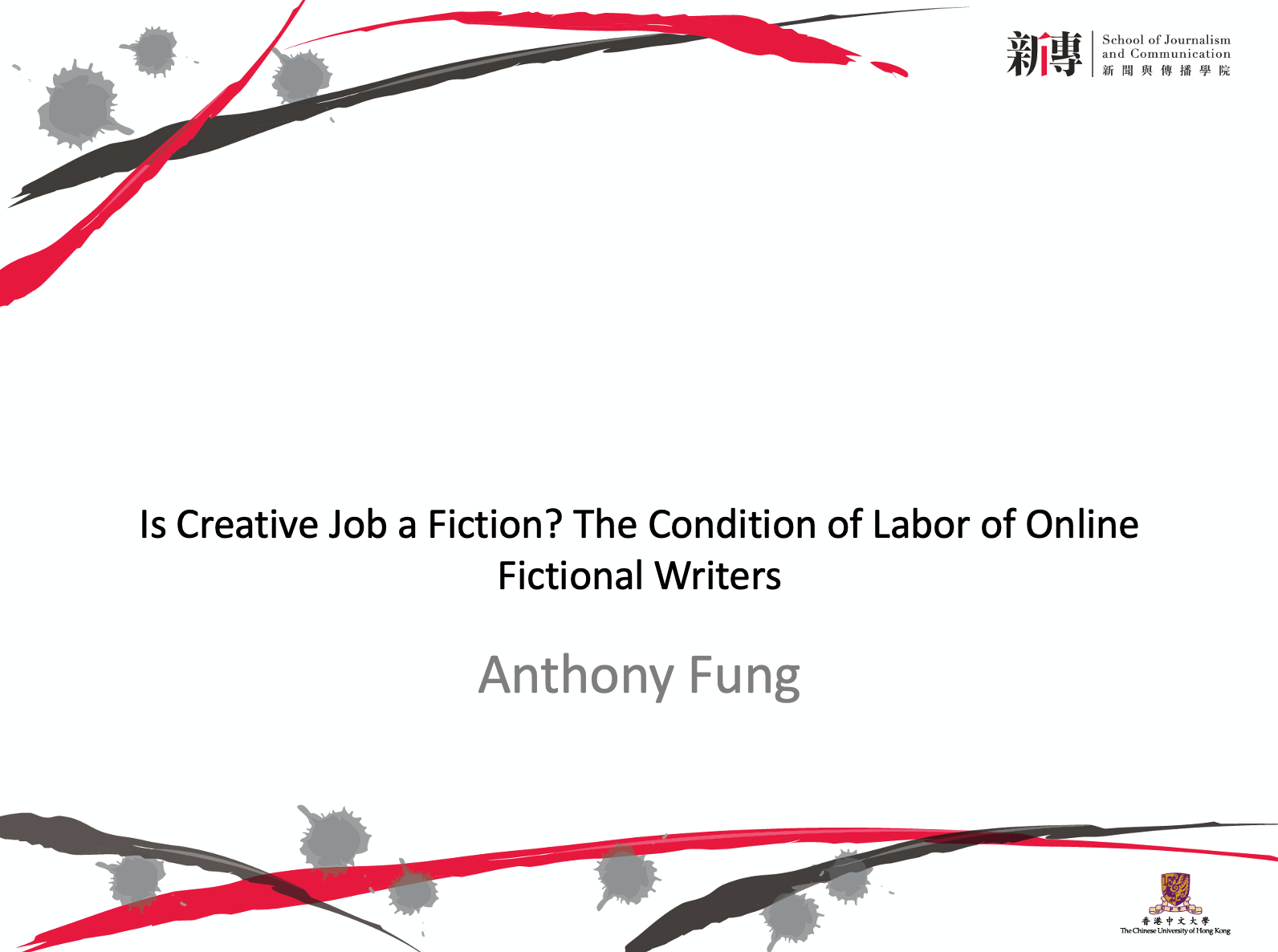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Terry Flew教授的演讲题目为《数字经济中的信任、沟通和治理:回顾与展望》。新冠疫情的爆发导致了民众对信息的特殊需求。信息需求被定义为“一种适应性的人类机制,驱动人类寻找、识别并适应社会和物理环境的变化”。媒介学说为以“信任”为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从20世纪70年代大众媒体研究中的“文化指标”,到21世纪的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互联网与“信任”,再到如今国际视野下的信任研究。新冠疫情恰好是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实验,以检验公民对其政府的信任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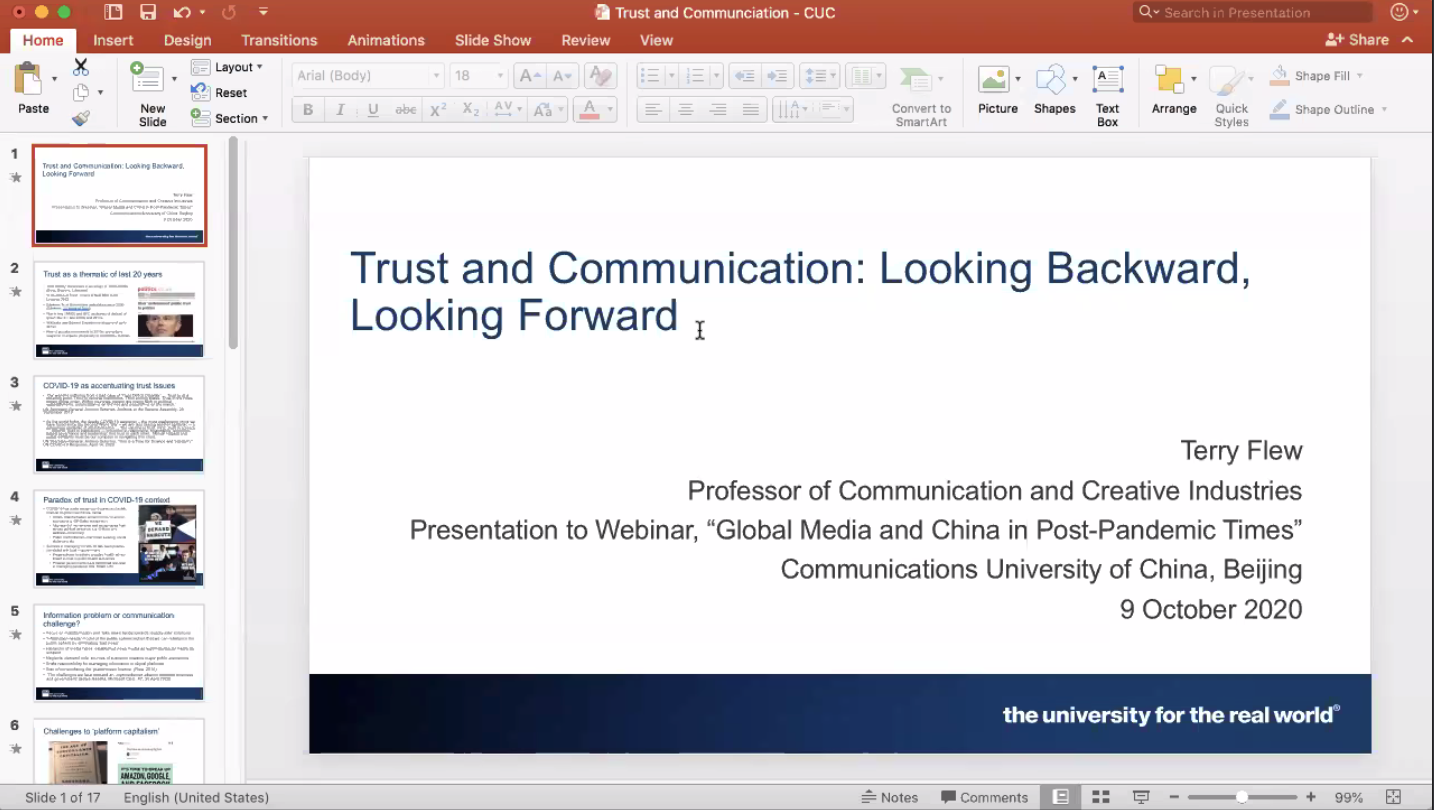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Michael Keane教授的主题演讲围绕《文化、技术、平台: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数字存在》展开。后疫情时代下,“线上”已然成为了一种“新常态”。数字文明的逐步生成、文化的产生变成了一种悬空的沉积过程。通过对“数字中国——从文化存在到创新国家2017-2020”的研究,希望能够解答关于中国能否借力互联网的“数字力量”一跃成为国际公认的创新型国家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性究竟如何这两个问题。该研究发现,亚太地区与澳大利亚五个地区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并不相同、了解程度也存在差异,这可能与媒体煽动、极端偏见与文化过滤的泡沫有关。


英国卡迪夫大学Stuart Allan教授以《新冠肺炎时代的科学新闻:公民科学与公民新闻的交互》为主题进行了演讲。“新”与“旧”媒体的融合正在重塑着科学新闻的格局,科学新闻中的假设是如何被设计以及是如何被改善的,值得我们密切关注。Allan教授在演讲中阐述了在疫情时代下塑造和引导科学新闻的几个重要动力,主要是通过致力与公民记者和公民科学家建立活跃的关系,并与他们共同对有关疫情的新闻报道展开流动的、交互的、不断推进的检验并阐明潜在的风险和启示。该研究还展示了几个来自不同国家的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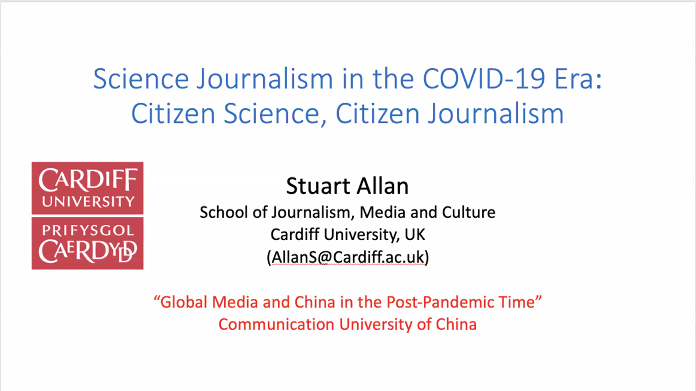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Jeroen de Kloet教授的主题演讲围绕《生物政治民族主义、情感启示与中国的新冠疫情》展开。通过比对各国疫情的发展情况,不难看出只有严格的管控才不会导致情况的失控。病毒不仅仅会被传染和感染,也会传播无从检测的惶恐与焦虑,公民骄傲于自己所在国施行的“最佳”和“最有效”的疫情控制办法。由此,公民的“生物政治民族主义”可以在躯体、地缘政治、情感间被动态理解。福柯关于“生物政治民族主义”的概念源于其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来进行国家与资本权力的运作,来用于管理人口以及更远大的用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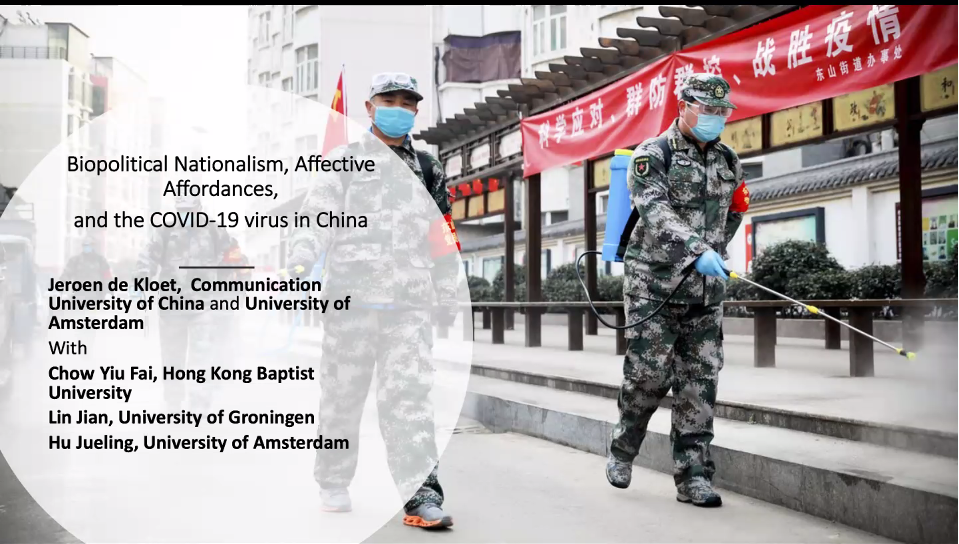
晚间的Global Media and China编辑部圆桌会谈由主编Anthony Fung教授主持,Fung主编对期刊2019年取得的成就和遇到的问题进行了简要阐述。各位编委围绕如何将期刊办得更好纷纷献计献策,大家表示,希望通过努力继续将Global Media and China打造成传播学及跨学科领域研究者云集的学术交流、展示的高端平台。
(编辑:阎玺)





 回到顶部
回到顶部